
法盛金融投资
致力于分享金融、不良资产、投融资、房地产、公司纠纷、私募基金、资本市场、税务筹划、疑难案例等干货。

“保底条款”作为一种增信措施,多见于委托理财、私募基金、资管产品等合同中。虽然一般被统称为“保底条款”,但实践中却是“一家三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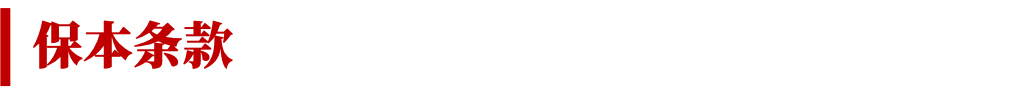
顾名思义,保本条款即为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双方在该种条款中约定,无论盈利或亏损,受托人均保证委托人的本金不受损失。而对收益方面,受托人则不做保底承诺,但会要求对收益分成。

在保本保固定收益条款下,受托人不仅保证本金不受损失,还向委托人承诺固定的收益。例如,受托人向委托人承诺保本且年收益20%或承诺保本且每月给与1.5%的“红利”。

保本保最低收益条款下,受托人不仅保证本金不受损失,还向委托人承诺最低的收益,对于超出最低收益部分受托人将要求分成。例如,受托人向委托人承诺保本且最低年收益20%,对于超过20%的收益则按受托人与委托人各50%分配。

此处虽说是委托理财合同,但实际上是除金融机构作为资产管理产品的受托人作出的保底承诺及私募基金管理人作出的保底承诺外的一般合同中约定的保底条款。但因多出现于委托理财合同中且理论及实务界对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讨论较多,因此以委托理财合同为典型。
传统观点中,认定保本条款及保本保最低收益条款属于无效条款。理由在于该等条款:一、违背市场规律;二、违背委托代理制度;三、违背公平原则。同时,因前两类保底条款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的核心条款,因此条款无效则合同无效;对于保本保固定收益条款,有观点认为,含有该等条款的委托理财合同属于借贷合同,应当按照借贷关系审理。
直到2018年,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申4114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中载明,“……《委托理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郑华作为受托人虽对证券买卖的收益作出承诺,但郑华作为自然人作出的上述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其所作出的证券买卖收益的承诺,并未导致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不违反公平原则。原两审判决认定《委托理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而该份《委托理财协议书》也因保底条款有效而幸免罹于“核心条款无效”。自此,对保底条款有效性的判定从墨守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和资本市场规则向尊重私法自治倾斜。
实际上在2018年之前,保底条款就有了守得云开见月明的盼头。例如,在2015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浙民申字第309号民事裁定书中载明,“……关于合同效力。案涉《受托资产管理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形式合法,内容亦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陈诺提出,案涉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了“由受托人承担全部亏损”这一保底条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然现行法律及行政法规并未从合同效力层面明确禁止委托理财合同作出上述保底约定,故陈诺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难以成立。”
本以为自2018年以后,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应当已经尘埃落定,但事实却是依旧扑朔迷离。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6民终4449号民事判决书中,直接认定了“系保底条款,应属无效”,且无任何说理。在该案件中,烟台中院并未就保底条款无效后合同是否有效进行论述及判决,但是从其要求返还投资款及利息的判决中可以推断出,烟台中院的观点亦是将保底条款作为合同的核心条款,核心条款无效则合同无效。
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民申4264号民事裁定书中,广东高院不光认为保底条款无效,而就保底条款无效后的损失承担根据过错比例进行了分配。但是在广东高院作出的(2019)粤民申8360号民事裁定书中则又认为“涉案《资产管理协议》、《欠款确认及房产抵押协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曹巍与胡秀兰有关损失承担与收益分配的约定相对应,具有均衡性,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可谓“同院不同判”。
除此之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新01民终2380号判决书则认为双方协议中的保本条款约定了按期收取相应比率的红利,期限届满收回本息,且协议并未约定投资风险承担的内容,故属于名为委托理财实为民间借贷之情形。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皖民初31号判决中,安徽高院虽然认可了受托人在承诺函中作出的保证委托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的承诺并认可了委托理财合同的有效性,但是判决理由确是别出心裁的“《承诺函》中表示自愿赔偿差额部分损失,并不能视为保底条款”。
再看回《九民纪要》第92条中规定,信托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资产管理产品的受托人与受益人订立的含有保证本息固定回报、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等保底或者刚兑条款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无效。从该条中倒是可以“品味”出以下几点:一、除金融机构外其他合同中涉及保底或刚兑条款,并非必然无效;二、保底或刚兑条款无效并不必然意味着其所在的合同无效,这也符合合同法中“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司法实践却如上述案例所展示的一样,可谓众说纷纭。且不论不同地区法院间裁判口径不同,即便在同一省市的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裁判中,结果亦是大相径庭。在《九名纪要》已经深入人心的后2019时期,裁判结果是否会向着更尊重私法自治的方向前进,我们拭目以待。

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涉的私募基金合同特指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而非合伙型或公司型私募基金合同。因为后两种私募基金合同不单涉及合同中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还涉及合伙协议、股东协议相关问题,故以后再作讨论。

讨论私募基金合同中保底条款的效力的前提是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性质。如若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金融机构,那么在《九名纪要》之后,更加肯定了保底条款无效的裁判口径。但是私募基金管理人是否属于金融机构,却暂无定论。
在金融机构的认定上,一般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金融机构编码规范》为标准。但是在《金融机构编码规范》中并未将私募基金管理人归入金融机构之列,唯一与私募基金管理人相关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虽是“基金管理公司”但并非等同于私募基金管理人,一方面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仅涉及证券投资,还涉及股权、债券等;另一方面,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是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设立则需要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手续。在一行三会印发的《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中亦未将私募基金管理人列入金融机构。
而在证监会发布的《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私募基金管理人被列为金融机构。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等6部门出台的《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中也将私募基金管理人列为金融机构。
虽然金融机构归类的口径并不统一,但是从目前的实践及主流观点看,并未将私募基金管理人纳入金融机构范畴。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私募基金合同争议普遍被归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这一案由。因此,理论上私募基金合同中保底条款及合同有效性的认定应当与前述委托理财合同案件基本一致,分别为:(1)条款无效且合同无效;(2)条款有效且合同有效;(3)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
但实际上,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具有金融机构“气息”的主体,法院在条款及合同有效性的认定上,不仅裁判依据有所不同,也远比一般委托理财合同更加谨慎。
首先,在条款有效性判定的依据上有别于一般的委托理财合同。除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民法公平原则外,判决中还涉及了《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一百零三条、《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等特别规定。
其次,保底条款有效的判决数量远小于一般委托理财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委托理财合同判决的“百家争鸣”,私募基金合同相关判例中保底条款效力几乎无一幸免。条款无效的理由,除违背市场规律、有违公平原则外,主要还包括以下两种:(1)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之规定,禁止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向投资者作出保底承诺,且保底条款免除了委托人应承担的投资风险,致使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失衡,违背了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和私募基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本原则,违反了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交易原则,诱导投资者非理性地将资金投入资本市场,危害资本市场稳定,进而据此认定条款无效。(2)参照《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根据该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作出保底承诺,其目的是为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基于“举重以明轻”的解释方法,连证券公司都不能在合同中约定保底条款,其他主体更不应在合同中作此约定。而判决保底条款有效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1)一般情况下私募基金管理人并非证券公司也非金融机构,故不适用《证券法》。(2)《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并非是法律或行政法规,且其中禁止私募基金管理人作出保底承诺的规定并非是效力性强制规定,因此不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最后,私募基金中保底条款无效不应必然认定合同无效。如前述,在一般委托理财合同中,一旦涉及保底条款无效,法院会以保底条款是合同核心条款为由认为合同无效。该裁判逻辑也被沿用到了私募基金合同纠纷中,例如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沪0115民初58930号判决中认为,虽然保底条款约定在《补充协议》中,但因保底条款为核心条款,因此保底条款无效必然导致合同整体无效。与该判例相对的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民终23878号判决,在该判决中广州中院仅因保底条款属于无效条款而否认了《补充协议》的效力,但是认定了主合同有效,该判决是合同条款可分割性的体现。笔者认为,在私募基金合同中,由于委托人应是“合格投资者”,且委托人在购买基金产品时不仅会考虑产品的收益与风险,也会考虑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管理等能力,因此不能再简单套用一般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的存在是委托人签订合同的根本目的这一逻辑。在私募基金合同中,若保底条款所保证的收益并非“畸高”,应当综合委托人自身能力、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资历、双方签订合同的背景等各方面来探求双方真实的缔约目的,而不能简单地将委托人视为单纯的“逐利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故即便保底条款被认定无效,合同本身未必罹于无效。

金融机构签订的资管协议中刚兑条款效力的认定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委托理财合同阶段。在该阶段金融机构签订的资管协议中的刚兑条款效力的裁判逻辑与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效力的认定基本一致,区别之处在于相较于一般委托理财合同,在法律适用上除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外还会适用《证券法》、《信托法》。
第二阶段是《资管新规》阶段,在该阶段裁判口径已经逐渐收紧。但是仍有观点认为,根据《资管新规》的规定,金融机构在资管协议中约定刚兑条款的后果是受到行政处罚,并非导致条款无效或合同无效。
第三阶段是《九民纪要》阶段,《九民纪要》明确了金融机构签订的资管协议中刚兑条款无效,自此刚兑条款效力的裁判口径应已统一。但如前述,虽然刚兑条款效力之争已尘埃落定,但是刚兑条款无效是否导致资管合同无效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笔者倾向认为,在金融机构的资管合同中,刚兑条款似乎并不再那么“核心”,刚兑条款应属投资者在购买产品过程中考量点之一而非唯一,除此之外,投资者还会关心金融机构的实力、产品本身的优劣等。因此即便刚兑条款无效,资管合同缔约双方的缔约目的并非一定落空,从《九民纪要》的表述上看,也为刚兑条款无效前提下裁判资管合同有效留有敞口。

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的效力目前仍处于众说纷纭的阶段;私募基金合同中保底条款鲜有有效判决;而金融机构签订的资管合同中的刚兑条款效力的裁判口径在《九民纪要》后应已统一为无效。
在合同效力的认定上,多数裁判采取了“全有或全无”的裁判口径,即条款有效则合同有效,条款无效则合同无效。值得注意的是,可以说“在合同无效的时候,没有一方当事人是无辜的”,若按照“全有或全无”的裁判口径将会得出一个有意思的悖论,那便是合同无效比条款无效合同有效对委托人更有利,换言之,有过错的委托人反而因合同无效而免于损失或承担小部分损失(目前主流观点是损失的20%),甚至还能获利(获得利息赔偿)。
笔者私以为,与其说保底条款的无效的最根本原因是阻止非理性投资、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不如说是对银行存贷款业务的限制。若允许非银行主体及银行在存贷款业务之外对外作出保本保收益条款,则与开展存款业务并无区别;而为实现保本保收益之目的,非银行机构及银行往往也会与被投资人签订保底保收益条款或回购条款,这便与贷款业务无异。故,通过保底条款,非银行主体能够绕开金融许可制度开展银行存贷款业务,而银行也能在存贷款业务外另开存贷款业务的“炉灶”,这必然导致金融监管的漏洞,最终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也许这才是保底条款无效最深层次的原因。

免责声明:本公众号发布的信息,除署名外,均来源于互联网等公开渠道,版权归原著作权人或机构所有。我们尊重版权保护,如有问题请联系我们,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