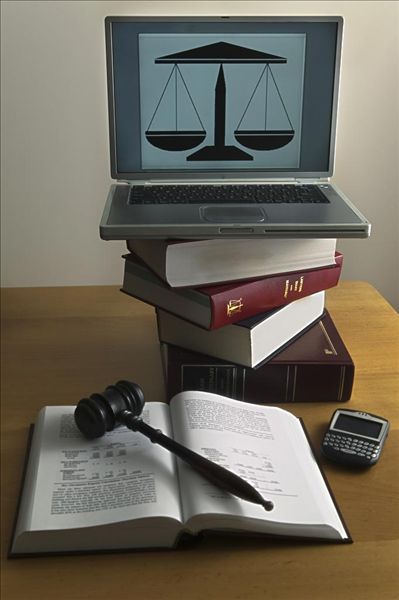
法盛金融投资
一个致力于分享金融投资、私募基金、不良资产、股权激励、税务筹划及公司纠纷、疑难案例干货的专业公众号,巨量干货及案例供检索。
摘 要:税务处理决定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间的关系一向是行政审判中的争议问题。司法实践中,法院存在三种裁判观点:征罚一体、征罚衔接、征罚并立。不同的裁判观点,产生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经考察税收征管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税务处理决定与处罚决定在实定法上并无先后之分,税务处理决定亦非基础性行政行为。二者的关系,还体现为税务处理决定在处罚决定案件中的拘束效力问题。税务处理决定作为行政行为,并无构成要件效力和确认效力;作为证据,其所认定的事实,不属于法院可以直接认定的事实。本文的结论认为,可采的裁判观点是经过修正的征罚并立观点,即税务处理决定与处罚决定是两种并立的但在事实认定上存在关联的行政行为,且处理决定对处罚案件不具有拘束效力。
关键词:税务处理 行政处罚 裁判观点
税务处理决定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间的关系(以下简称“征罚关系”)一向是行政审判中的争议焦点问题。实践中,税务稽查机关的做法不一,有的同时作出税务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有的先作出税务处理决定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相对人方面,有的一并起诉两个决定,有的因经济能力问题无法对税务处理决定申请复议,遂只起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意图“曲线救国”一并推翻税务处理决定。
一、实践中税务处理决定与处罚决定关系的司法裁判观点
在税务稽查机关同时(或先后)作出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而相对人仅对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法院需要考虑征罚关系。对此,法院存在不同的做法。经梳理相关案例,主要有三种裁判观点。试析如下:
(一)征罚一体
征罚一体观点认为税务处理决定与处罚决定所认定的违法事实是一体的,不分彼此。在贵州金星啤酒有限公司诉安顺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案中,二审法院所持的是征罚一体观点。二审法院认为:“但该税务处理决定系本案被诉安国税稽罚〔2015〕1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基础性和关联性行政行为,该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的金星公司少缴增值税、消费税税额同时成为本案被诉税务处罚决定的事实根据。……为了全案的妥善处理,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该税务处理决定所认定金星公司增值税、消费税偷税金额亦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判决变更,……”二审法院以《行政诉讼法》第77第1款规定为据,在判决主文中变更了税务处理决定中的相关认定及处理结果。
虽然该案中法院认为处理决定是处罚决定的基础性行政行为,表面上是持后将述及的征罚衔接观点。但是,在该处罚决定案件中,当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税务处理、处罚决定不一致时,不仅讼争的处罚决定都要按法院的认定予以变更,税务处理决定也要一并变更。因此,从该案的判决方式看,征罚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一体关系。即使原告没有对税务处理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基于“征罚一体”思路,事实上将税务处理决定纳入税务行政处罚案的审理对象并作出判决。这种判决方式,有利于彻底解决税务争议,解决税务行政处罚纠正后、违法税务处理决定仍继续有效的尴尬境地。
当然,这种判决方式也存在可商榷之处。首先,存在是否超诉讼请求判决的问题(尽管这就是原告内心所要达到的效果)。毕竟,从行政法角度,税务处理决定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是不同的行政行为,即使原告同时起诉了,法院的通常做法也是分别立案、合并审理、分别判决。对原告未起诉的行政行为进行审理和判决,法理上尚难周延。其次,二审法院为支持“征罚一体”而援引的法律依据,在理解和适用上也需要再探讨。《行政诉讼法》第77第1款规定:“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该款旨在扩大了变更判决的范围,从旧法的行政处罚扩大到其他行政行为。这是从诉讼的整体而言,即法院既可以对行政处罚案件作出变更判决,也可以对其他行政行为案件作出变更判决,丰富了可判决变更的案件类型。但从该款似难以解读出在个案中对行政处罚的变更也可以延及关联行政行为的变更。
(二)征罚衔接
征罚衔接观点认为税务处理决定所认定的违法事实是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又可称为“征为罚基”观点。在白山市浑江区温馨鸟名店诉白山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案中,一、二审法院对案涉税务处理决定在本案中的作用的见解一致,二审法院认为:“白山国税稽处〔2016〕2号税务处理决定已确定温馨鸟名店应当补缴增值税的税额,且该税务处理决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此,白山国税稽查局依据上述规定对温馨鸟名店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符合法定程序。”无疑,法院认为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对税务行政处罚案具有拘束力。而且,法院在判决的事实部分对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在理由部分对处理决定认定的结论照单全收,不再对相关证据进行评判。
相同的案例还有郑州手拉手集团有限公司与郑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处罚案。该案中,税务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同日作出。一审法院在事实部分叙明如下:“2015年6月8日,被告对原告作出郑地税稽处〔2014〕6020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查明原告的违法事实为,……以上税款合计2034112.07元。同日,被告作出郑地税稽罚〔2014〕6020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原告存在上述处理决定中认定的违法事实,认为原告采取虚假纳税申报的手段少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2032953.78元,企业所得税1158.29元,已构成偷税,……”一审判决理由在援引《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第1款后阐述如下:“被告所作的郑地税稽处〔2014〕60201号税务处理决定中,认定原告存在不缴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少缴企业所得税的违法事实,该处理决定未经法定程序予以撤销,被告据此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符合规定。”二审法院判决理由亦只有一段话,但援引的法律依据更具针对性:“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被上诉人所作的郑地税稽处〔2014〕60201号税务处理决定中,认定上诉人存在不缴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少缴企业所得税的违法事实。该处理决定未经法定程序予以撤销,被上诉人据此对上诉人进行行政处罚符合规定。”
征罚衔接观点的理据在于:1、税务处理决定相较于处罚决定,具有基础性地位。虽然两个行政行为可能同时作出,但内在逻辑上,税务处理决定“先于”处罚决定。2、行政行为具有存续力。税务处理决定生效后,其对法院审理处罚决定案件具有拘束力。
(三)征罚并立
征罚并立观点认为税务处理决定与处罚决定是不同的行政行为,税务处理决定所认定的违法事实对处罚决定案件并无拘束力。在合肥晨阳橡塑有限公司诉长丰县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再审案中,税务稽查机关先后作出了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晨阳公司仅对税务行政处罚提起诉讼。虽然《税务处理决定书》也是本案的证据,但再审法院在判决理由关于事实认定的评判中对《税务处理决定书》只字未提。
此外,也有一审法院持“征罚衔接”,但二审持“征罚并立”。例如,在中山市交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与中山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处罚案中,一审法院判决理由认为:“市地税稽查局于2013年8月12日作出中山地税稽处(2013)10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责令交安公司缴纳上述款项,……但交安公司未提出复议申请,即交安公司对其少缴的税款金额未依法提出异议。在此基础上,市地税稽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交安公司处以2010年度少缴的营业税62544元……,合计370104.04元,合法合理。”二审法院虽然维持原判,但在判决理由中却没有提及上述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对税务处理决定也是只字不提。
二、税务处理决定与处罚决定关系的实定法规定及评析
无论征罚关系采取哪种观点,首先还是要看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是如何规定的。
(一)《税收征收管理法》和《税务稽查工作规程》之解读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纳税人伪造、变造、……,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是违法事实,同时“偷税”还是定性。该句是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都必须查明的事实。“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规定的是两种法律后果,应注意该句中的“并”字,“并”前是处理决定,“并”后是处罚决定。但从“并”字的文义来看,有“同时”的意思,并没有孰先孰后的意思。可以说,税务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是并列的两个行政行为。
同样,《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4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该款中,“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都要认定的违法事实。其后的规定,是两种并列的法律后果。
法条的结构是“构成要件(违法事实)+法律后果”。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税法法条中,构成要件(违法事实)是同一的,而法律后果有两种,由不同的行政行为负责。正如税务实务人士指出:“两份文书基本上‘共用’同一违法事实,只是处理结果的‘分工’不同,前者是补缴税款和滞纳金的决定,后者是基于少缴税款的一定比例的处罚决定。”笔者认为,可以打个比方,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关系图形是同一根树干上的两个枝桠(形同“Y”)。因此,征罚衔接观点不成立,两种行为不存在孰先孰后问题,也不存在谁为基础问题。
当我们再考察税务稽查的实际运作规定,恐怕还会有出人意表的发现。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简称《规程》)规定,税务稽查工作由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个环节组成。选案、检查是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共用的。检查结束时,检查部门制作的《税务稽查报告》内容包括税务处理、处罚建议及依据。在审理环节,开始出现分叉。《规程》第51条规定:拟对被查对象或者其他涉税当事人作出税务行政处罚的,向其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第52条、第53条规定了听取陈述、申辩和组织听证等事项。第51条至53条规定的是处罚的程序。那么,在处罚程序进行的这个阶段,处理决定程序是自走自的吗?从《规程》后续规定看,是等着。可以想见,如果在处罚程序中发生了对违法事实的改变,处理决定也必然要跟着改变。根据《规程》第54条规定,审理完毕,审理人员应当制作《税务稽查审理报告》,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检查人员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被查对象或者其他涉税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情况;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税务处理、处罚意见及依据等。第55条至第57条规定了处理决定书和处罚决定书的制作。也就是说,从稽查程序上看,处理决定要等处罚的告知、听证等程序走完才能作出!某种意义上讲,处理决定要以处罚程序为基础。这就颠覆了“处理决定是处罚决定的基础性行政行为”认知。
(二)“纳税争议”之争议
当然,税务机关为了减轻举证负担,避免败诉风险,还是希望处理决定在处罚决定案件中具有拘束力。于是,有的税务机关祭出了“大杀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0条。《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0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纳税争议,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对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及退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而发生的争议。”税务机关以上述规定为据,认为处罚决定认定的构成要件(违法事实)属于“纳税争议”,当事人若有异议,应走税务处理决定的救济途径,在税务行政处罚案件中不得争执。这一观点得到一些法院支持,如前述郑州手拉手公司税案。
但也有法院不予认可。例如,在泰州市圣达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与江苏省兴化市国家税务局处罚案中,兴化国税局针对圣达公司的上诉辩称:“圣达公司上诉的主要理由是针对税务处理决定中关于销售额及应纳各类税款的计算依据及方法,即‘纳税争议’提出的异议,该上诉理由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纳税争议’属于税务行政处理范畴,是行政处罚的事实基础,上诉人对税务处理事实部分的全部证据,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且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就被上诉人作出的税务处理行政决定申请法律救济,上诉人起诉时税务处理决定已生效,在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认定的纳税数额有重大明显错误的情形下,再行就此提出异议无法律依据。税务处理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的正确性和处理决定书的有效性应予确认……”二审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对税务机关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回应,只对事实和证据进行阐述:“上诉人2011年少缴增值税59703.86元……。上述事实由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予以证实,而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故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有事实依据。上诉人诉称的涉案行政处罚认定的实际收入和其他应税收入数额错误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言外之意是,处罚决定有没有事实依据,只关乎证据,与处理决定无关。
笔者认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0条规定的“纳税争议”,应指的是一个整体的行政行为,即包含“构成要件(违法事实)+法律后果”的行政行为。税务机关将构成要件(违法事实)抽出来作为处理决定独享的一部分,显然忽视了处罚决定作为一个行政行为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事实上将处罚决定作为处理决定的附属行为。因为,按该说法,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不是共用一个构成要件(违法事实),而是处罚决定借用处理决定的构成要件(违法事实),征罚关系图形由枝桠型(Y)变成嫁接型(y),处罚决定成了嫁接于处理决定树干上的一根枝。依此逻辑,日后税务机关作出处罚决定时,事实部分表述:“依据本局发生法律效力的税务处理行政决定,你单位存在如下违法事实:……”在应诉时只提交《税务处理决定书》和处罚程序性证据,而不提交其他实体事实证据,法院该如何是好?一般情况下,法院不会认同这个做法。毕竟,法院还是需要通过审查证据来判断税务处理决定是否无效。即使持“征罚衔接”观点的白山温馨鸟名店税案,法院也在证据清单后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作了认定。更何况,处理决定所认定的构成要件(违法事实)的质地没有那么纯,如前所述,构成要件(违法事实)要经过处罚程序(告知、听证)才能最终认定。因此,以“纳税争议”为由排斥法院对处罚决定所认定事实的审查,理由是不成立的。
三、税务处理决定的效力问题
征罚关系问题的实质,是税务处理决定在处罚决定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更确定地说,法院要考虑处理决定对处罚决定案件有没有拘束力。采征罚一体观点,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互无拘束力,但是判决支持或否定一个决定,就必然要判决支持或否定另一个决定。采征罚并立观点,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也是互无拘束力,但是判决支持或否定一个决定时,对另一个决定则不予置评。征罚一体和征罚并立实际上并无本质不同,只不过前者是法院对税务处理决定介入过深,后者则根本不介入。就法院对税务处理决定介入程度而言,处于二者之间的是征罚衔接观点。该观点认为处理决定对处罚决定案件具有拘束力。这就涉及税务处理决定的效力问题。
税务处理决定的效力,可以从两个具有互相关联的角度来考察。
(一)税务处理决定作为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
虽然从上述法条分析,可以否定税务处理决定“基础性”行政行为的地位,但税务处理决定作为行政行为的效力,仍是征罚关系绕不开的问题。主张征罚衔接观点的理据之一是税务处理决定具有存续力(或者确定力、公定力),因而对法院审理相关案件具有拘束效力。然而,在行政法学中,行政行为对其他国家机关的拘束效力,不是放在存续力的概念范畴下,而是在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和确认效力中探讨。
构成要件效力是指对于一个已生效的行政行为,其他行政机关以及法院应将该行政行为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要件予以承认、接受,并作为自身决定的基础。构成要件效力原则上只针对行政行为的主文部分。关于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对法院有多大拘束作用?在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领域争议较大。但法院有权对行政行为作合法性审查的情形下(如行政审判领域),行政行为对法院并无构成要件效力,这点是无争议的。然而,当法院审理A行政行为时,已生效的B行政行为对法院是否具有构成要件效力,则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具有构成要件效力,但在征罚关系中并不适用,本文在前述关于“纳税争议”的部分已作论证,在此不赘。
确认效力同样也是行政行为对其他国家机关产生的拘束效力。与构成要件效力不同的是,确认效力针对的是行政行为的“事实与法律认定”(即行政行为的理由部分)。然而,法院判决理由是否具有既判力都尚且有争议,遑论程序的缜密性与严谨性都远不能及的行政行为?因此,德国通说认为,行政行为具有确认效力,以法律有特别规定为限。在我国,亦无立法规定税务处理决定具有确认效力。
(二)税务处理决定的证据效力问题
在税务行政处罚案件中,《税务处理决定书》以证据形式进行司法审查视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可资对照的有两项规定。《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70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税务处理决定书》显然不在其中,但如果“征罚衔接”观点把握不准度的话,很容易达到第70条的效果。《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8条规定,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那么,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是否可以适用这一条?笔者认为,恐怕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情况下,生效的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如无相反证据推翻,可以作为法庭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类行政行为,要么是外在于被诉行政行为,与被诉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有部分交集;要么是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或前置行为。而且,这类行政行为往往先于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或证据。而税务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是“共用”同一违法事实,该违法事实按稽查规程是同时且合一认定(虽然决定文书制作可能有先有后),以税务处理决定来证明处罚决定所认定的违法事实,属于“自己证明自己”,在证据规则上缺乏正当性。
实践中,已有法院明确否定了在征罚关系中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的违法事实可适用《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8条和第70条规定。例如,在绍兴市越城区牌口士明砂石厂诉绍兴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处罚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处理决定中认定的违法事实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中“法院可以直接认定的事实”,也不属于该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的“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事实。
四、结 语
综上,征罚关系的三种裁判观点只是法院对税务处理决定介入程度的不同判决方式。若以处理决定对处罚案件是否有拘束效力来划分,实际上只有两种观点:征罚衔接观点和经过修正的征罚并立观点。经过修正的征罚并立观点不认为处理决定对处罚案件具有拘束效力,但承认在构成要件(违法事实)的认定上,二者是一体的。本文通过对实定法的评析,否定了税务处理决定是基础性行政行为的观点;从行政行为理论和证据规则两个维度进行探讨,否定了税务处理决定对法院具有拘束效力。从而,征罚衔接观点具有法理上的重大缺陷,经过修正的征罚并立观点是可采的裁判观点。
基于此,笔者概括以下税务处理决定与处罚决定案件审理思路:
一是,税务处理决定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是两种并立但存在关联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若同时起诉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应当分别立案、分别判决,可以合并审理。
二是,行政相对人只起诉处罚决定而未起诉处理决定的(下同),税务机关应提交作出处罚的全部实体性证据和程序性证据,实体性证据不能只提交《税务处理决定书》。
三是,法院在审理处罚决定案件时,不宜对处理决定进行评判,无论是肯定性还是否定性评判。
四是,法院基于事实认定问题撤销或变更处罚决定,可以发出司法建议,建议税务机关纠正处理决定。但是,法院基于违法情节考量而撤变处罚决定的除外。
五是,同上述第四点情形,相对人也可以以法院判决书为据,向税务机关申请重新作出税务处理决定。税务机关拒绝重新作出决定的,相对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
注 释:
[1]在我国台湾地区,征罚关系亦有不同观点。我国台湾地区“最高行政法院”2009年8月第二次庭长法官联席会议就“漏税罚之所漏税额可否推估”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其中“所漏税额应否受推计核定处分拘束”即涉及征罚关系问题。参见葛克昌:《税捐行政法——纳税人基本权视野下之税捐稽征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3-485页。
[2] 参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4行终27号行政判决书。
[3]例如,在河南理工大学与焦作市地方税务局税务行政管理案中,原告一份诉状同时起诉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一审法院也作为一个案件受理了,并作出判决。二审法院则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如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应当对不同行政行为分别提起诉讼,而不能请求人民法院在同一次诉讼中对不同的行政行为一并审查。……因理工大所诉涉及多个行政行为以及多项诉讼请求,理应分别起诉,故理工大在一份诉状中对不同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不符合行政案件的起诉条件,其起诉应予驳回。”参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8行终121号行政裁定书。
[4]参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6行终13号行政判决书。
[5]参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行终588号行政判决书。
[6] 参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合行再终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书。
[7] 参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中中法行终字第105号行政判决书。
[8]“并”字在汉语中有“不同的事物同时存在,不同的事情同时进行”之意,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2页。
[9]徐战成等编著:《涉税裁判案例启示录(第二辑):增值税与所得税典型案件深度评析》,企业管理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
[10]参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中行终字第00053号行政判决书。
[11]根据行政行为理论,行政行为作出后告知(送达)即生效,并非要过了争讼期才生效。
[12]关于行政行为的存续力、确定力、公定力理论评述,参见赵宏:《法治国下的行政行为存续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255页。笔者赞同赵宏教授以行政行为存续力替代确定力、公定力的观点。
[13]关于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和确认效力,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许宗力和大陆地区学者赵宏均有深入的探讨。本文相关基本理论,主要参考两位学者论著。参见许宗力:《行政处分》,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上)》(第3版),台湾地区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17-522页;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308页。
[14]首届“中国税法实务论坛”上,有税务实务人士提出税务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在认定违法事实上的证明标准不一,处罚决定适用的证明标准更高;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并不影响税务处理决定的事实认定效力。会后,亦有税法学者向笔者提出这一问题。笔者回应:“假设相对人对税务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都提起了行政诉讼,而法官依据不同的证明标准,肯定了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的违法事实,却否定了处罚决定认定的违法事实。那么,舆论会认为法官得了精神分裂症。”但是,笔者经阅读税法著作,发现上述税务实务人士和税法学者的观点有其依据,那就是如果税务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分别走不同调查程序、适用不同证明程度时(如德国税法),法院的审查密度亦应有所不同,该观点参见葛克昌:《税捐行政法——纳税人基本权视野下之税捐稽征法》,第484页。然而,如果税务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是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同一个法条作出,且在违法事实认定上走同一个程序流程,此时,两者的证明标准难有区别可言。
[15]参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行终75号行政裁定书。
[16]第五点涉及“行政程序的重新进行”制度,类似于诉讼中的再审。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可资借鉴,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00-304页;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217页。

免责声明:本公众号发布的信息,除署名外,均来源于互联网等公开渠道,版权归原著作权人或机构所有。我们尊重版权保护,如有问题请联系我们,谢谢!

